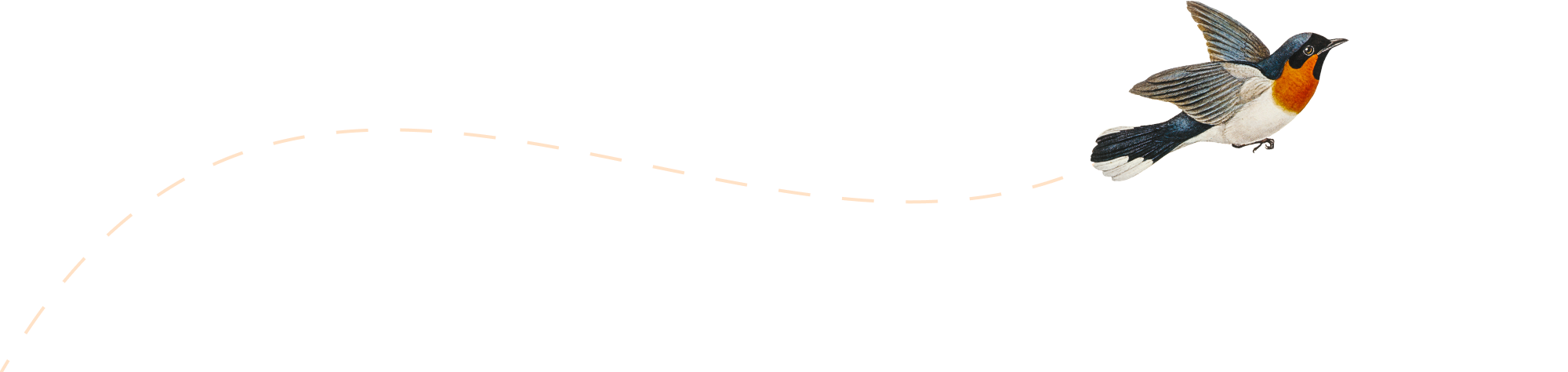这两天有点失序,事务太多,时间又紧,自己的精力管理却是不够。
北京的雾霾天气让人没有脾气。
吃饭的时候看了篇小说,于建嵘写的《我的父亲是个流氓》
我以久不看政治多年,虽然相比我的不少朋友,我还算是个政治动物。最近环球时报抨击变态的民国热,说每个时代都会有些人物以各种各样的原因去怀念故国,当年的王国维和辜鸿铭,现在知识分子圈。
我也曾经民国热了好久,现在也还热着,当年上大学甚至在境外网站注册参加了一个中国泛蓝联盟这样一个组织,想去打印店打印青天白日旗放在自己作为自己的logo。
然后不得不承认,环球日报这种看似扯蛋的文章,说得并无大错。
虽然这国家有千种病万样糟,然后正如那句话讲的,有什么样的民众就有什么样的政府。
仓廪实而知礼节,虽然对于士人来说,此条并不一定成立,然而对于大众来讲,免于饥饿才是最基本的人权。
我厌恶这样的国家,厌恶这样的人民。但是我生于这样的国家,我周遭尽是这样的人民。我也流着这样的血。
无论我心中为着那些民国的先烈们,那些傲骨有些多么深沉的怀想,那个时代也已不会再来,所能做的不过是多少继承些当年的风骨,在这片肮脏的土地上做点什么。
虽然对这血污的旗帜实在是没有半点好感。
我爷爷24年生日,今天即将满九十,身体还硬朗,每次回家总要与其聊天很久,落成文字的东西却不够。
他告诉说在他们那个年代,整一个乡没有多少人识字,山上土匪横行,据说有个叫刘寡妇的极为厉害。
我爷爷曾经和和老爷一起趁一个国民党士兵撒尿的时候缴了他的枪,两个人提着枪在老家附近漫山遍野地寻找一个仇人。
我老爷抽鸦片,在日本占领期间经常穿梭在镇上和老家倒腾东西。那时去镇上不是件容易事,老爷是个典型的蛮人加浑人,曾经在对着我爷爷说,妈巴子的,你是我爹。然后叫我爷爷叫了一天爹。
爷爷告诉我说那时节,基本不能出门,出门一定被抢。当时国民党军队打仗基本靠跑。战斗力差得一塌糊涂。
我不知道在爷爷脑海中还有多少历史鲜活地保存在那里,告诉我之前家里在河对岸,家里养过匹黄马,告诉我我们村当时文化大革命闹得还不是很凶。可是那里沟的谁也被斗死了。
爷爷讲这些话的时候没有什么情绪,除了比平时显得更有精神之外。
包括他自己的故事,包括别人的故事都像是发生在另一个世界。说起来像和当下的时空不发生一点联系。
小村里的生活比较简单,可是最古老的房子也都是七十年代留下来的。
历史没有痕迹,只有风化,不管曾经多么英雄壮举,多么见解深刻,多么美人如花,最后都淡化成遥远的故事,甚至让人怀疑到底是否发生过。
我的父亲是个英雄,曾经在黄河源头有顺流下来,冲波逆折的劲头是他们那一代人所特有的对自然的征服与最朴素的所谓无产阶级革命豪情。
我父亲的黄河漂流队,在我父亲被挺着大肚子的母亲拉回来的时候,刚过完一个险口,那个险口,队里的八个人死了四个。
前几年央视报道那个年代的黄河漂流,提了那几个死去的人名字,雷建声,郎保洛。我父亲当时看着那个节目,心中也不知做何感想。
我父亲当年在牢房中听着外面有人放鞭炮,问狱警发生了什么,狱警说过年了,我父亲说当时泪流满面。
我父亲说他当年做革命小将被选派成河南省革命代表到清华宣传经验,当时大字报贴了一墙全是他的名字。
我一直对那个年代人的感情没有一点理解,直到去年在学校看到一个老画家的画展,锈迹斑驳的工厂和老火车,落下的大雪,满目的夕阳,整个画的色调只有淡黄与暗灰,我突然感觉到那中低沉的颜色下埋藏着什么东西。
我在那个瞬间才理解我的父亲,理解他为什么会对毛有那种感情,会因为被人说长得像毛,而兴奋。
那是他们的青春,他们的年代,他们的热血。
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我混乱不堪,我对这片土地和这土地上的人民怀着一种爱恨交织,五味杂陈的感觉。
我们的年代早已经没有主题,我们的朋友也早已经没有共识,在追求个人幸福的主题下,每个人定义着不同的幸福场景,我们生活在一个失去意义的年代,需要自己主动去建构意义,而建构出来的意义,扔在这个喧嚣的世间就像一滴水掉入喷发的火山岩。
从一个物质匮乏的年代步入一个精神匮乏的年代,极少的人能理直气壮着对着世界说自己为什么在活在争。
我曾经说我要探索世界的奥秘,帮助别人成长。
停顿一下,还好,虽然这一篇虚无主义的文章中,写下这句话,我仍然感觉到一丝暖意。
可是很多时间,看着这句话,想着这百年来四代人的艰辛转折。
家国仍然是个不解的名字。
路尚远。天还未亮。